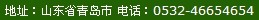|
北京有哪些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姓名:林品个人介绍:我是一位“哈利·波特”系列的“学者粉”(aca-fan)——既是一位学术研究者,希望能够像纽特那样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像卢平那样给学生带去启迪与帮助;也是一位奇幻爱好者和Coser,希望能够和同好们一起,在那个既令人亲切又充满惊奇的魔法世界当中,纵情驰骋我们的想象,尽情飞扬我们的梦想,共同创造丰富多彩的“哈迷文化”。霍格沃茨是我的母校●我最重要的成长伙伴作为世界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J.K.罗琳和她的“哈利·波特”系列已经是无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三十年之前,一位身材瘦削的十一岁男孩,突然跃入了正搭乘火车从曼彻斯特前往伦敦的罗琳的脑海——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顶着一头蓬乱的黑发、前额处有一道细长的闪电形伤疤……伴随着车轮与铁轨的合奏,罗琳为这位男孩取名为“哈利·波特”。在那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这位男孩从火车旅客的突发奇想,成长为了灵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的生命世界也化作文字、被搬上银幕,陪伴着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读者,度过了我们的成长时光。我是在自己读初一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哈利·波特”的。我看着哈利走进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从十一岁长到十七岁;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读完了“哈利·波特”系列的七本书,从十二岁长到了十八岁。对我来说,哈利就如同我的一位成长伙伴,我和他一起在霍格沃茨接受了宝贵的教育,同时也因霍格沃茨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从叙事学的角度上说,“哈利·波特”是一部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长篇小说。虽然原著并不是以哈利的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我们观察魔法世界的视野却是由哈利的视角所限定的,哈利的所见所闻也就是原著读者的所见所闻。(有一些哈利无法置身其间的场景,他也能够通过梦境,通过他与伏地魔之间的奇妙的心灵联系,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知。)这样一种文学创作手法让我很容易代入到哈利的角色位置,并由这种角色代入产生出强烈的情感共鸣。更进一步说,“哈利·波特”系列的一大魅力,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许许多多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而哈利作为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视点人物,无疑可以说是那么多角色当中获得作者最多笔墨的一位,因此也是人物性格展现得最为丰满的一位。在罗琳的笔下,哈利既会展现出正直善良勇敢的一面,也会暴露出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这一点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暴露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他的优点,还是他的缺点,我们读者都一览无遗。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因为这种多维度、多面向的呈现,让我觉得哈利是最为真实的一位人物,也是和自己有着最多共通之处的一位角色。我在自己的青春期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和心理问题,而在阅读“哈利·波特”的过程中,我会彷佛揽镜自照一般,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哈利也陷入一些相似、相通的生活与心理困境。而他在困境当中的坚强应对,他从霍格沃茨的同学那里获得的贴心安慰,他从霍格沃茨的师长那里获得的谆谆教诲,曾给身陷青春沼泽的我带来过极为重要的勇气、慰藉和启迪,他的所作所为会反过来影响和塑造我的现实应对方式,他的所思所想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塑造我的心态乃至三观。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不仅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和哈利的共通之处,而且是这种阅读本身就在让我变得越来越像哈利。林品与“哈利·波特”译者马爱农老师我和他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那个魔法世界的thechosenone,而我只是一名平凡的麻瓜。或许曾经以为,只要在自己生日那天的午夜,默默闭上眼睛,就会有一个巨人怀揣着魔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兴冲冲地到来;或许曾经以为,只要瞄准着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之间的墙壁奋力冲去,就可以进入一片充满魔力的天地;或许曾经以为,只要鼓足勇气,就可以骑着扫帚飞行;或许曾经以为,只要念个咒语,就可以变出奇迹……但时光的洪流却将这些天真烂漫全都冲走,“长大”的我习得了“现实”,也习得了“平凡”。但和哈利身处的那个魔法世界一样,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也不只有魁地奇、黄油啤酒和荧光闪烁,还会有摄魂怪、乌姆里奇甚至黑魔标记。而在这个同样善恶交织的麻瓜世界中,我一直都坚持携带着我从哈利那里获得的勇气和启迪,携带着我从霍格沃茨学到的真知,努力书写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当我“不得不在正道和捷径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也总是会回想起那一位“正直善良勇敢的男孩”……●我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程时光荏苒,我已从一名“霍格沃茨学子”变为一名大学老师,而“哈利·波特”也成为了被推荐阅读的书籍。今天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在我身处的班级里,阅读“哈利·波特”曾经是一件触犯禁忌的事情。当年,正值“中二期”的我会煞有介事地在自己的中学课程和霍格沃茨的魔法课程之间一一建立对应。而在我的课程比对中,语文课对应的是黑魔法防御术,这既是因为语文课是我心目中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因为我的语文课和哈利的黑魔法防御术课存在着一个奇特的巧合——授课老师更换得特别频繁。我的语文老师在三年的时间里换了四任,而哈利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则是在七年里换了七任。我高一时候的语文老师是一位相当开明的先生,我的Cosplay首秀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完成的。那是在年的秋季学期,学校举行诗歌朗诵比赛,绝大多数同学都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与语文读本中挑选了文学史上的经典诗歌作为朗诵篇目,而我却选择了自己撰写的一首悼念小天狼星的原创诗歌。早在中考结束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就从网上购入《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的英文版,一手捧着沉重的原著,一手翻着厚如板砖的词典,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艰难地将书读完。在这场阅读之旅的结尾,我惊愕地目击了小天狼星的牺牲,随即将盈眶的泪水化作那首悼亡的诗歌。为了更加淋漓尽致地演绎那首诗歌,我决定装扮成哈利的样子去进行朗诵,以便更为真挚地进入悼念小天狼星的抒情氛围。正是在那位语文老师和我的家人的共同支持下,我从一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网站购置了一套霍格沃茨校袍和格兰芬多围巾,在我还从未听说过“Cosplay”这个概念的情况下,完成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Cosplay表演。不过,我高三时遇到的语文老师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三来了,禁止你们再读长篇小说。”在她的教学方案里,高三的时间应当尽可能地用来在题海里奋战,而不能“浪费”在“课外闲书”之上。然而,我高三的秋季学期,恰逢“哈利·波特”第六部出版,像我这样的“霍格沃茨学子”怎么能放弃自己的“魔法学业”呢?于是,我就背着那位“麻瓜老师”,在课后争分夺秒地抢读最新出版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而在阅读“哈利·波特”的过程中,我会有意识地在小说阅读与知识积累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循环。从赫敏的名字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信使,从她被扣上“泥巴种”蔑称的经历到种族主义的漫长历史,从她发起的家养小精灵解放阵线到现代社会的平权运动,在我的脑海当中,“哈利·波特”的故事元素与人文社科的知识点不断发生诸如此类的互文关联,前者的感性力量与后者的理性力量相互激发,增强了我的感悟与理解,进而塑造了我应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反对偏见,反对歧视,追求平等,包容多元。不仅如此,我还会去深究“哈利·波特”的故事情节与世界观设定背后的灵感来源与文化积淀,将浓厚的阅读兴趣转化为持续的求知动力,借助各种课外书籍与网络渠道,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而依照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学术经典的提示,形成自己的知识图谱。由此获得的阅读体验与批判性思维,由此拓展的知识结构与跨文化视野,也为我的作文增添了很多独异于人的灵感与创意。然而,在高三年级的语文教研组里,却还有另外一位老师,不但多次给我的作文打了很低的分数,而且还直接来找我谈话,声称他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我放弃那种在他看来“根本不适合高考考场”的作文风格,劝说我模仿他的议论文模板来进行写作。面对两位语文老师的施压,我再次从“哈利·波特”中汲取勇气。我将他们视作哈利五年级时遭遇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思想僵化甚至滥用职权的乌姆里奇,同时非常“中二”地将自己代入到反抗乌姆里奇的“邓布利多军”的位置,努力在高压之下继续坚持自己的阅读方式与写作风格,继续葆有自己的棱角与个性。林品与北大教授戴锦华老师最终,我考取了我们市那年的高考文科最高分,成为全市唯一一位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并且在进入北大燕园的第一个学期,就将自己多年的体验与遐想转化为十五万字的文稿,出版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著作《我的哈利波特:哈7大猜想》。大三时,我更是将“哈利·波特”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调动自己的生命经验,运用我在北大课堂上习得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个既深刻地影响了自己、也广泛地影响了自己同代人的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展开深入的探讨,最终完成了一篇五万字的本科学年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指导老师的高度评价,以及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最高分,这也带给我很大的信心,激励我走上了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我们的霍格沃茨校友情除了原著小说之外,由“哈利·波特”的精彩故事与丰富设定衍生而来的系列电影与同人文化,同样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那些年,我们曾在各自的台灯下、被窝里,为着从纸墨中飘飞出的幻梦奇遇,时而悲戚,时而欢喜;那些年,我们也曾信手徜徉于赛博空间,发布我们的同人,讨论我们的CP,彼此吐槽,互相嬉戏;那些年,我们还曾经与那些相交莫逆抑或萍水相逢的哈迷一起,结伴融入黑色的神秘,对着光影交织成的诡谲瑰丽,齐声发笑,并肩哭泣……而在“哈利·波特”系列的观影经历当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场景出现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结尾处:当时,邓布利多校长惨遭杀害,黑魔标记笼罩在霍格沃茨城堡的上空;然而,环绕着邓布利多遗体的霍格沃茨师生并没有就此放弃,只见他们纷纷举起手中的魔杖,向天空施放“荧光闪烁”的魔法,仰拍镜头中,一点点星光在霍格沃茨的上空集聚,渐渐地照亮了那片夜空,驱散了邪恶的黑魔标记……央视节目录制现场对我来说,这个场景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这个场景象征着“哈利·波特”系列所蕴含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即便身处弱势,即便暗夜沉沉,我们依然永不言弃,我们依然要联合起有限的力量,来对抗邪恶的强权,来捍卫人间的正义。相信每一位读完整个系列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并不是一片“童话般的净土”,其中也有沉重的挫折,也有难熬的苦难,也有令人窒息的绝望,也有撕心裂肺的离殇——一如那些童年之墙崩塌时我们所遭遇的现实,一如我们在合上书本、走出影院之后所要面对的生活。在那里,我们曾见证小天狼星猝然落入帷幔彼岸,我们曾见识粉衣官僚露出的奸诈阴毒的恶笑,我们曾见证吐蛇的骷髅闪烁在被闪电击中的城堡之上,我们曾见识被控制的魔法部如何向所谓的“泥巴种”张开大屠杀的罗网……但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才可以切实地汲取那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我们看到,从洁白的坟墓中,飞出一只涅槃重生的凤凰;我们看到,双胞胎乘着扫帚,在乌姆里奇的头顶燃放自由的烟花;我们看到,卢娜送来慰藉,金妮目光坚毅,纳威慨然奋起,哈利、罗恩、赫敏,坚定地迈出战斗的步履;我们看到,凤凰社和D.A.的勇士们大无畏地冲破了极权统治下的自我保全逻辑,英勇地肩负起“同有史以来最邪恶的魔头斗争”的崇高使命……在这些场景与事迹中,我们学到了如何从挫折中培养坚强,学到了如何从苦难中得到磨练,学到了如何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学到了如何从离殇中懂得珍惜,学到了如何在逆境之中坚持爱和正义。另一方面,上述场景还联系着我的一段具体观影经历。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哈利·波特”八部连映活动中,我与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哈迷朋友一同观看到邓布利多陨落的场景。当时,我们也和银幕上的霍格沃茨师生一样,高举起自己手中的魔杖,用这样的方式传递我们的哀思,表达我们心意的凝聚。因而,在我的心中,这个场景还象征着我与哈迷朋友围绕“哈利·波特”展开的“趣缘社交”,象征着我们因“哈利·波特”而缔结的宝贵友谊。林品与哈迷朋友我在八部连映活动上结识的北京魁地奇俱乐部,就是这种“趣缘社交”的绝佳代表。出于对“哈利·波特”的热爱,全球各地有许多心灵手巧的哈迷朋友,相继根据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对罗琳发明的“魁地奇”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由巫师骑着扫帚在天空中飞行的运动改造为麻瓜提着扫帚在绿茵场上奔跑的运动。年初,这项运动由杭州外国语学校的王佳晟同学从美国引入中国,随后又由保送至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刘谊颖同学从杭州带到了北京,刘谊颖同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的李扬聃同学合作创办了北京魁地奇俱乐部,并且在年秋天举办了第一次活动。而在年春天的八部连映现场,身着格兰芬多魔法袍的我面对面地结识了身着拉文克劳魔法袍的李扬聃与刘谊颖,同时还有许多来自四大学院的霍格沃茨校友也都以此为契机,加入了北京魁地奇俱乐部的网络群组。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北京魁地奇俱乐部联合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外交学院等多所高校的科幻奇幻社团与学生会,以及“哈迷有求必应屋”这样的哈迷组织,举办了很多场魁地奇友谊赛乃至魁地奇联赛。北京魁地奇俱乐部对我们来说,“麻瓜魁地奇”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是一种以魁地奇体验为核心内容的哈迷聚会,一种围绕共同兴趣展开的“趣缘社交”。我们这一代哈迷大多都是独生子女,而且都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长大的,因而难免会陷入到孤独而疏离的“原子化生存”的境遇当中。但是,借助互联网络和社交媒体,通过线上的交流和线下的聚会,我们能够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作为因缘的纽带,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趣缘社交网络”。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浪潮中,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这种并非基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纽带、也并非基于功利考虑的趣缘社交,为我们带来了一种特别珍贵的情感联结。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对于“哈利·波特”的兴趣爱好,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种因缘纽带,牵引着我与许许多多志趣相投的哈迷朋友,在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相遇、相识、相知。这种友谊,至今依然紧紧地陪伴着我;这份霍格沃茨校友情,就像斯内普教授的守护神一样,闪耀着恒久的光芒,Always……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13801256026.com/pgyy/pgyy/8222.html |
当前位置: 围巾 >林品霍格沃茨是我的母校齐鲁晚报网
时间:2025/1/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秋天围巾怎么搭配好看
- 下一篇文章: 去不了霍格沃茨的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假装有